盗窃罪之“财物”释义与反思
浏览量:时间:2016-06-26
盗窃罪之“财物”释义与反思(一)
——以“保安冒充房主私自出租房屋案”为切入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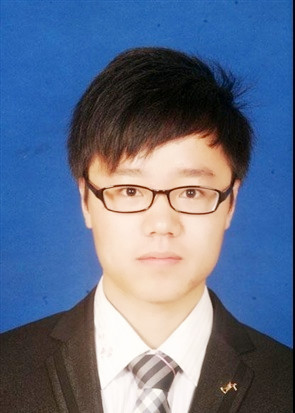
曹富乐
(作者:曹富乐,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硕士,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与任职单位无关。)
一、案情介绍
二、分歧意见及案件争议焦点
房主刘某看到王某正在开自家门,误以为王某正在实施犯罪,在制止王某的过程中,袭击并造成王某轻伤。刘某的行为应当构成假想防卫。按照传统刑法理论,对于假想防卫,应当根据认识错误的处理原则:行为人有过失的,以过失犯罪论;行为人没有过失的,以意外事件论。本案中,房主刘某并不存在过失,而且刑法分则只规定了过失致人重伤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因此,刘某不构成犯罪。
租户王某未经刘某允许,私自进入并使用刘某的房屋,但其行为系受保安钱某冒充房主出租房屋行为的误导。此外,王某与李某(保安钱某冒充房主所使用的假名)签订租房合同并交付了租金。因此,王某无主观罪过,不构成犯罪。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保安钱某的行为在刑法上应当作何评价。一种观点认为钱某构成盗窃罪,另一种观点认为钱某不构成犯罪。即本案争议的核心在于钱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有少数观点认为,钱某构成诈骗罪。刑法通说认为,诈骗罪(既遂)的基本构造为: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受骗者)产生(或继续维持)错误认识——对方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害。本案中,保安钱某确实采取了欺骗的手段(冒充房主),使王某产生错误的认识(认为钱某就是房主),并且基于该认识处分了财产(与钱某签订租房合同并且支付了10万元租金)。关键在于,王某支付10万元租金后已然获得并实现了1年的房屋使用权,其并未遭受财产损害。换言之,王某并非本案的被害人。因此,钱某构成诈骗罪的观点不能成立。
行为是认定犯罪的关键。分析案件事实可以发现,钱某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冒充房主将房屋出租于他人,并将租金据为己有。此行为能否构成盗窃罪呢?换言之,“冒充房主并私自使用别人的房屋租赁权”是否构成盗窃罪呢?更进一步说,“房屋收益权”能否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呢?
三、盗窃罪之“财物”释义
《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根据刑法的明文规定,盗窃罪的犯罪对象为“公私财物”。然而,关于“财物”的刑法范围问题,刑法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由于不动产的特殊属性,对于不动产是否属于盗窃罪之“财物”问题,存在较大争议(此问题将会在后文中详细讨论);另一方面,随着司法实践中窃取财产性利益行为的日益猖獗,对于财产性利益是否属于盗窃罪之“财物”问题,学界争议更大,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随着财产性利益保护需求的增多,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越来越倾向于肯定说的观点。对此,应当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对于“财物”的刑法范围进行界定。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其最经典的表述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其最主要的使命是在公民自由与国家刑罚权之间划出界限,保护公民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恣意侵害。贝卡利亚将罪刑法定原则视为刑法的第一要义,其指出:“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只有代表根据社会契约而联合起来的整个社会的立法者才拥有这一权威。任何司法官员(他是社会的一部分) 都不能自命公正地对该社会的另一成员科处刑罚。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因此,任何一个司法官员都不得以热忱或公共福利为借口,增加对犯罪公民的既定刑罚。”
在追求自由和人权的当代,作为限定公权力、保障私权利之盾的罪刑法定原则已然成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不得逾越的屏障。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规定被认为是我国刑法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的规范依据。尽管学者对该规定的内涵理解不同,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是毋庸置疑的,其对刑事立法和司法都有着绝对的限制意义。可以说,“罪刑法定主义首要使命是对立法权的限制”,同时,“罪刑法定主义还意味着以立法权限制司法权”。因此,无论是刑事立法还是司法解释都必须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刑法禁止类推、不成文法、事后法以及绝对不定期刑。在刑事立法和推行司法解释的过程中,判断规范是否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一个重要标准即在于立法条文和司法解释是否有违刑法用语的含义,从而有违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只有国民能够根据现行刑法规范合理预测自身行为的刑法性质时,才能够发挥刑法预防犯罪的机能,才能够真正意义上限制国家公权力,尊重和保障人权。
(二)财产性利益不属于盗窃罪之“财物”
对刑法条文的解释必须结合具体规范,在自身的语境下进行。《刑法》第264条将盗窃罪的犯罪对象明确限定为“公私财物”,根据《辞海》的定义,“财,是金钱物资的总称”;“物,在法学上指依法能为人所支配控制并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一切物质资料。可按各种标准进行分类,主要有: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禁止流通物、限制流通物与流通物;动产与不动产;原物与孳息;有体物、无体物与特殊形式物等等。”
我国刑法语境下的“财产性利益”这一概念来源于日本,日本刑法将财产犯罪的对象分为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例如《日本刑法》第336条第1项规定诈骗罪犯罪对象限于“财物”,第2项规定,“以前项方法,取得财产上的不法利益,或者使他人取得的,与前项同。”所谓财产性利益,“是指除了财物以外的具有财产价值的某种利益,常见的有使人负担对自己的债务,使人免除自己所负的债务、接受他人提供的劳役等等。”
从规范角度,关于财产性利益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最早可以追溯到罗马法时期。盖尤斯在《法学阶梯》写道,“有些物是有形的,有些物是无形的。有形物是可以触摸的,例如:土地、人、衣服、金子、银子以及其它无数物品。无形物是那些不能触摸的物品,它们体现为某种权利,比如:遗产继承、用益权、以任何形式缔结的债。”从内容上可以看出,罗马法中的“无形物”和现代法学上的“无形物”并非一个概念,其更类似财产性利益,之所以表述为“无形物”可能在于当时并没有“抽象权利”这一概念。从财产性利益的内容(债权、债务、收益权等)可以看出,财产性利益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抽象思维所拟制的产物,而非客观存在。“尽管客观世界不存在该物的实体,但一旦人们将之抽象出来,它就会对人们的行为施加影响,甚至成为法律所规范的对象。”如前文所述,《辞海》中“物”在法学概念上属于物质资料。而所谓物质,“是指与‘精神’相对,不依赖于意识而又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也就是说,“财物”从语义上说应当属于“物质”,是“与精神相对的客观实在。”因此,“财物”和“财产性利益”并非种属关系,两者分属两个范畴,“财物”的语义不包含“财产性利益”。如果将财产性利益作为盗窃罪之“财物”,必然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
从实践角度,首先,争议之所以存在,恰恰是因为“财产性利益不是财物”,而刑法条文将盗窃罪的犯罪对象限定为“财物”,以至于对侵犯财产性利益的行为无法规制。因此,为了司法实践的需要,将财产性利益突破性的纳入财物之范畴的观点应运而生。换言之,如果财产性利益本身就是财物的一种,司法实践出现了侵犯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当然可以并且应当适用刑法的相关规范,何以会产生如此大的争议?日本刑法明确将财产犯罪对象分为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两类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其次,肯定论者依据《刑法》第265条以及盗窃罪相关司法解释,论证其观点的合理性。且不说司法解释能否作为学理论证的依据,单以《刑法》第265条属于注意规定来论证“财产性利益属于财物”这一逻辑本身就颠倒了因果关系。(具体原因,后文将详细阐述)实质上,认为财产性利益属于盗窃罪之“财物”的理由,主要在于司法实践中侵犯财产性利益行为的剧增。但是,试图通过这种方式破解司法困境的思路值得警惕。无可置否,随着社会的发展,财产形式的扩张,侵犯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与日俱增,对这类行为规制的要求愈加迫切。然而,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即使社会危害性再大,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为犯罪的,必须做无罪处理,这是现代刑事法治的基本内涵。司法实践的需要,只是违法行为犯罪化的立法依据,而不能作为解释规范的依据。对于司法者而言,必须坚持“规范在前,价值在后”的立场。因此,无论从应然角度还是实然角度,盗窃罪之“财物”都不应当包含财产性利益。
四、案件结论
由上文可知,本案争议的核心在于“房屋收益权”是否属于盗窃罪之“财物”?盗窃不动产侵犯的是不动产所有权,显然“房屋收益权”虽然涉及不动产,但其性质无法归于“不动产”。具体而言,刑法中的财产性利益主要包括:“(一)对被害人设定权利,如使被害人房屋出租交与使用;(二)使被害人免除加害人或第三人债务,如使书立免除债务字据或退还借据;(三)使被害人提供劳务,如使演员演出;(四)使被害人满足加害人或第三人之欲望,如给付白饮白食、免费观剧、乘车等;(五)其他获得财产上之受益,如窃占他人之土地耕种之收益、占据他人房屋居住等均属财产罪之不法利益范围。”毫无疑问,“房屋收益权”属于财产性利益。因此,钱某不构成盗窃罪,其行为属于民法的侵权行为。值得一提的是,《刑法》第245条规定了非法侵入住宅罪,但该罪侵犯的法益是个人居住的平稳、安宁权(关于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法益,存在争议,主要有安宁说、公共秩序说、占有说、住宅权说、综合说、相对化说等。本文认为,按照刑法分则体例,非法侵入住宅罪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结合司法实践,采取安宁说无疑更为合适。因此,钱某不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的间接正犯。
案例分析告一段落,但对于“财产性利益是否属于盗窃罪之‘财物’”的争议,尤其是肯定论者的逻辑思路,值得检视和反思,具体内容且听下回分解。
免责声明:本网部分文章和信息来源于国际互联网,本网转载出于传递更多信息和学习之目的。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立即联系网站所有人,我们会予以更改或删除相关文章,保证您的权利。


 全国免费咨询热线:
全国免费咨询热线:
 皖公网安备:
皖公网安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