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罪立法及司法解释的定性与反思
浏览量:时间:2016-07-28
盗窃罪立法及司法解释的定性与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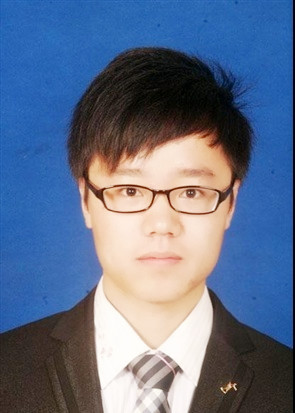
曹富乐
(作者:曹富乐,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硕士,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盗窃罪中,涉及财产性利益的规范主要有:《刑法》第265条(以下简称第265条)规定,“以牟利为目的,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或者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4条第三款规定,“盗窃电力、燃气、自来水等财物,盗窃数量能够查实的……”;《解释》第5条规定,“盗窃不记名、不挂失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的,按照下列方法认定盗窃数额……”;《解释》第9条规定,“偷开他人机动车的,按照下列规则处理:(一)偷开机动车,导致车辆丢失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一、《刑法》第265条定性及反思
关于财产性利益是否属于盗窃罪之“财物”,《刑法》第265条是肯定论者主要的规范依据。从逻辑思路上,肯定论者以“第265条是注意规定”为由,以论证财产性利益解属于盗窃罪之“财物”。这一逻辑进路应当质疑。
所谓注意规定,是指“在刑法已作基本规定的前提下,提示司法人员注意,以免司法人员混淆或忽略的规定。”与注意规定相对应的概念是法律拟制。
所谓法律拟制,“是指立法者基于某种价值目的的考虑,不论事实上的真实性,有意用现有的法律概念、法律规范去解释和适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将不同事物等同对待并赋予其相同法律效果,从而达到既能适应社会需要又能体现法律基本价值之目的的立法技术或立法活动。”
注意规定和法律拟制都属于刑事立法活动,两者不同之处在于:注意规定并没有突破现行法律规范,只是对基本规范内容的重申,规定的有无不影响结论;而法律拟制是一种法律上的假定,其并不受既定法律规则和常规法律逻辑的限制。
判断某一条文属于注意规定还是法律拟制,应当依据既定法律规则和理论。很明显,肯定论者预设结论的合理性,通过将第265条定性为注意规定,论证“财产性利益”属于盗窃罪之“财物”,这一思路明显陷入循环论证的漩涡。退一步说,即使第265条属于注意规定,我们也无法从“他人通信线路或者电信码号”属于盗窃罪之“财物”推导出“财产性利益属于盗窃罪之‘财物’”这一结论。(事实上,针对第265条的犯罪对象“他人通信线路或者电信码号”的性质本身就存在争议,有学者主张其本身为无体物,而不是财产性利益。按照此观点,第265条确实为注意规定,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肯定说的论证。对此,为了方便论证的展开,本文直接将“他人通信线路或者电信码号”的性质视为财产性利益。)其以特殊论证一般的逻辑思路,很明显属于类推。
追根溯源,判断第265条属于注意规定还是法律拟制,必须依据既定刑法规范和刑法理论。在中国,无论是79年《刑法》还是97年《刑法》,都将盗窃罪的犯罪对象规定为“公私财物”。从规范和理论的角度,财物在语义上无法包含财产性利益,而第265条将财产性利益性质的“他人通信线路或者电信码号”作为盗窃罪犯罪对象,无疑是突破了刑法的一般性规定。因此,如果认为“他人通信线路或者电信码号”属于财产性利益,刑法第265条理应是法律拟制。如此一来,才能够在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消弭刑法第265条和第264条的冲突。
值得思考的是,“法律上之拟制,适当地使用时,无论对于何人,皆不生损害。”但是,应当看到,通过法律拟制的手段能够将从本属于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规范合法化,但其不意味着法律拟制不受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恰恰因为法律拟制具有创设犯罪与刑罚的立法功能,而又不受法律理论和既定法律规则约束的属性,使得法律拟制具有相当大的风险性,其更需要罪刑法定原则的严格限制。法律拟制具有随意控制犯罪圈范围的能力,其仅限定于立法活动的范畴,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因此,法律拟制的主体仅限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无论如何都不能进行法律拟制活动。同时,立法机关对法律拟制的设置必须保持极其审慎的态度,必须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即对于适用民法等其他法律足以规制的行为,禁止设置法律拟制进行调整,否则将会严重威胁到公民的自由和人权,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相背离。换言之,法律拟制应当为实现公平正义的目的而设置,其正当性应当体现为其既能实现刑法保护社会的价值,也不妨碍刑法人权保障机能的发挥。
二、相关司法解释的定性与思考
罪刑法定原则还意味着以立法权限制司法权,否则司法擅断将不可避免,而“罪刑法定原则对司法权的限制最突出的就是对刑法司法解释的限制”。因此,司法解释只能遵循刑法规范进行规范意义的解释,而不能超越刑法规范的内涵进行解释。换言之,刑法允许适当的扩大解释,禁止类推解释。因此,廓清扩大解释和类推解释的界限至关重要。对此,张明楷教授在深入研究后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形式上,扩大解释得出的结论并未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是在刑法文义的‘射程’内进行解释;类推解释得出的结论超出了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是在刑法文义的‘射程’之外进行解释;第二,从着重点上,扩大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本身,是对刑法规范的逻辑解释;类推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之外的事实,是对事实的比较;第三,从与立法原意的关系上,扩大解释是对立法原意的明确化;类推解释是在立法原意之外主张解释者自己所设定的原理;第四,从论理方法上,扩大解释是扩张性地界定刑法的某个概念,使应受处罚的行为包含在该概念中;类推解释则是认识到某行为不是刑法处罚的对象,而以该行为与刑法规定的相似行为具有同等的恶害性为由,将其作为处罚对象;第五,从实质上,扩大解释没有超出公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类推解释则超出了公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笔者对此区分界限深表赞同。可以看出,解释的内容是否超出现行规范的语义范围是判断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形式界限,也是首要标准。
以此为标准,可以明确盗窃罪相关司法解释的性质。如上文所述,“财物”在语义上包括有体物和无体物,《解释》第4条将电力、燃气、自来水等确定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符合刑法用语的日常意义,并没有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属于文理解释。《解释》第9条规定,“偷开机动车,导致车辆丢失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对此,可以理解为:偷开机动车本身并不能构成盗窃罪,只有偷开机动车并导致车辆丢失才构成盗窃罪。由此可以看出,该条解释并未将“机动车使用权”纳入盗窃罪犯罪对象,而将规制对象限定为“机动车”本身(机动车本身属于“财物”)。因此,该条解释完全符合盗窃罪的一般规定,属于文理解释。《解释》第5条将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归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对于此解释存在较大的争议。肯定说认为其属于扩大解释,并将其作为论证“财产性利益属于盗窃罪之‘财物’”的规范依据。但不难看出,“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等财产性利益已经超出“财物”的“射程”,我们不能着眼于刑法规范之外的事实,以“相似行为具有同等的恶害性”为由,试图将其定性为扩大解释。显然,该条解释属于类推解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
值得说明的是,文理解释应当是法律解释首选的解释方法,一般情况下,通过文理解释已经能够明确刑法条文规范的含义时,不能再采用其他解释方法。有肯定论者试图通过体系解释的方法论证其观点的思路并不恰当。此外,虽然说,处罚的必要性能够为明确扩大解释和类推解释的界限提供一定的参考,但前提必须是在语义可能具有的含义“射程”内。也就是说,如果解释内容超出了刑法规范语义可能具有的含义,不管刑罚处罚的必要性有多高,都不能进行解释。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也是现代刑事法治的要求。
应当看到,我国存在着诸多类似于第5条这类具有类推解释性质的司法解释。司法机关试图通过司法解释,设置具有法律拟制属性的规范,这也意味着,司法机关越权行使了立法权力。不可否认,相较于刑法条文规范,司法解释更具有灵活性和明确性,并且能够及时弥补“法律漏洞”。但是,“从逻辑上说,司法解释赖以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与必要性并不能成为证成其‘立法化’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论据”。可以说,具有类推解释性质的司法解释,不仅无法成为学理论证的规范依据,其效力本身也应当被予以否认。如果承认类推司法解释的效力,则相当于赋予了司法机关设置法律拟制的权力,也就意味着司法机关具有立法权。如此一来,司法机关便可以通过法律拟制的手段,随意的将刑法上并未明文规定为犯罪但又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这也就意味着,公民的人权和自由随时面临着公权力的践踏,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随之荡然无存。因此,我们应当坚决否认具有类推解释性质的司法解释法律的效力,更应当在刑法解释过程中守住罪刑法定原则的底线。
三、余论
关于盗窃罪之“财物”的刑法范围,应当结合《刑法》第264条的具体规定,在罪刑法定原则的视野下予以明确。结合“财物”的法律语义,不动产应当属于盗窃罪之“财物”,财产性利益则不属于盗窃罪之“财物”。如果行为人侵犯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触犯其他犯罪,则可以以其他犯罪处理,否则,只能作无罪处理。
司法实践中,类似于冒充房主出租房屋的行为层出不穷,例如就餐逃单、打车后逃跑等,对于这类行为的刑法规制确为必要。同时,应当明确,刑事处罚的必要性不能作为类推解释的正当性依据,但对于推动刑事立法意义重大。
《刑法》第92条规定,“本法所称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是指下列财产:(一)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二)依法归个人、家庭所有的生产资料;(三)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合法财产;(四)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债券和其他财产。”《辞海》中对于财产的定义是:“财产,是指金钱、财物和民事权利义务的总和。按财产是否具有实物形式,可分为有形财产(如金钱、财物等)与无形财产(如知识产权等)。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可分为有形财产(如知识产权、债权等)与消极财产(如债务等)。”因此,从刑法条文规范和法律用语的语义上,财产性利益应当属于“财产”的范畴。相对于法律拟制手段而言(如设置第265条),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将《刑法》第264条中的“财物”直接修改为“财产”无疑更为合适。这样既解决了司法实践的难题,也迎合了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的体例。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导下,这一思路同样可以适用于其他罪名相同困境的解决,如抢劫罪、诈骗罪等等。
同时,应当看到,在相关争议的背后,作为现代刑事法治“精神支柱”的罪刑法定原则面临着重重威胁。对此,刑事立法应当保持克制,诸如《刑法》第265条这类法律拟制条文的设置,应当严格予以限制。而作为立法和司法连接桥梁的司法解释,其功能应仅限于对刑法条文规范含义的进一步解释。但现实中,诸多司法解释“以解释之名,行立法之实”,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越权解释已经成为类推制度废除后罪刑法定原则最大的敌人。必须严格禁止越权解释。无论是刑事立法还是司法解释,都应当坚守保障人权的底线,恪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否则,刚刚萌芽的罪刑法定原则将成为“在现实领域明亮而一无是处的彩灯”。
免责声明:本网部分文章和信息来源于国际互联网,本网转载出于传递更多信息和学习之目的。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立即联系网站所有人,我们会予以更改或删除相关文章,保证您的权利。


 全国免费咨询热线:
全国免费咨询热线:
 皖公网安备:
皖公网安备:



